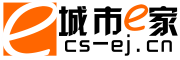内容提要:清末民初的小说撰稿者多用字号、笔名对作品进行署名,这不仅给读者及研究者造成了困扰,也使得对撰者的判定常常出现错误,如误以为“太常仙蝶”是陈蝶仙的别号,误以为尤玄甫与尤墨堂是两个人等等,同时还容易引起关于作品是否涉嫌“抄袭”的争议。随着小说撰者及小说产量的增多,对清末民初小说作者的随意署名就需要特别地加以留意,这不仅有助于厘清作品归属、撰者姓字等基本事实,对于处理越来越重要的署名权、版权等问题也有借鉴意义。
本文地址:http://motor168.cxdr.cn/news/119.html
珂云塔 http://motor168.cxdr.cn/ , 查看更多